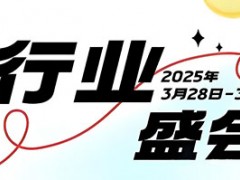围绕“关于日中佛教交流”这一主题,中日两国参加本次会议的8位代表做了基调发言和演讲,中国佛教代表团4位代表发言分别是:湛如《唐代长安西明寺与日本佛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錩《谈汉文佛教文献数字化总库建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文良《中日近代的<大乘起信论>研究与中国的近代佛学》、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琪《赵朴初与当代中日佛教友好交流》。
湛如在题为《唐代长安西明寺与日本佛教》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唐代长安城是中国佛教的中心,而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国化佛教体系形成,辐射至日本、韩国,最终形成了大乘佛教为主体的文化圈。
以下为湛如演讲内容摘编:
西明寺始建于唐高宗显庆年间,五代后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寺院位于唐长安城延康坊西南隅,在今西安市白庙村一带,是唐代最大的寺院之一,有房舍四千多间,日常还承担着皇室的礼仪祷告活动,僧人众多。西明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众多,首先它是唐代国家供奉的几座寺院之一,保存有唐代御造经藏;其次它是国家译场,玄奘、义净、不空等曾在此翻译众多经典;再次是道宣、怀素、圆测、善无畏等都曾在此驻锡,与南山律宗、东塔宗、法相宗西明系、密宗渊源深厚;最后是众多留学僧在此求法,将西明寺学风流传世界。
中日学者的研究,使西明寺与日本佛教的关系,清晰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明寺与中日佛教关系提供坚实的基础。
法水东流:求法僧在西明寺的活动
在唐代,西明寺作为国家译场,高僧汇集,曾经在西明寺弘教、受戒、修习过佛法的中外僧人为数众多,寺僧如昙旷等甚至影响敦煌。正因其强大的影响力,吸引了众多国外留学僧驻足学习。日本僧人永忠、空海、圆载、圆珍、道慈等都曾在西明寺住留。这些留学僧人,在中国首先学习的是佛法,同时学习中国各种文化。
这些带回日本的文化中,最出名的是道慈以“西明寺”为模具,参与“大安寺”的设计建造一事。这些来中国学习的留学僧主要以学习佛法为主,同时也将中国的书法、音乐、茶艺、建筑布局等带回日本,使中日之间的佛法体系一脉相承。
源远流长:西明寺文化体系对日本学僧的影响
西明寺除名僧聚集外,也以丰厚的典藏而闻名:“显庆年际西明寺成,御造藏经”,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西明寺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众多僧人著作频出,根据藏中诗侬芙的统计:“长安西明寺学僧们的著作,如参与西明寺创建的玄奘翻译的76部1347卷经典、西明寺上座道宣的35部188卷著作、西明寺道世的12部156卷著作等。”
这些统计表明西明寺的学风经历了阶段性变化:最初是玄奘一系的翻译系;接着是道宣、道世的编撰系,最后是未被统计的善无畏密宗系。这三系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举足轻重。西明编撰文化对民间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在《寺院文化空间与小说创作》文中提到,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记载的故事,出现在敦煌写卷S.4037与P.2094中,并有所发展,形成回鹘文。这说明西明寺的文化体系同时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而不是单纯的从西域吸收后往东传播。
上述材料中,西明寺三个时期不同的学风,不仅对中国本身的佛教文化发生重大作用,同时对日本来华的留学僧也产生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当留学僧回国后,这些影响也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
硕果累累:留学僧对日本的贡献
唐代是中国佛教宗派大发展的时期,形成了法相宗、华严宗、密教、禅宗、净土教等各个宗派。
西明寺和其中的一些宗派有着极深的渊源,众多留学僧在西明寺学习,受到这些宗派影响,回国后著书立说,开宗立派,推动日本佛教新一轮的发展。除佛教典籍外,这些留学僧回国后对日本文化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圆珍将入唐期间与各地士子、名僧、诗人的著作集成《行历抄》流传于世,为日本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保存很多重要的文学文献,还有一些中国《全唐诗》未收的诗歌。
西明寺不仅在唐代佛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它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约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前后吸引了空海、圆珍、道慈等日本留学僧前来求法。在不同的时间段中,西明寺形成的不同学风对日本佛教产生了巨大作用,甚至为真言宗的建立提供基础。留学僧在带回佛教典籍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其他文化带入日本,进一步推动日本佛教发展。
西明寺的文化系统不仅对东方的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西部的敦煌也产生不可忽略的作用,昙旷、乘恩都是西明寺系的大德,在敦煌讲学弘教。因此,西明寺不仅对唐代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影响,也对促进东亚地区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