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因素对一种语言的影响,或许无过于佛教对汉语的影响了。至今,汉语中仍有不少源于佛教的常用词,如“世界”、“实际”、“究竟”、“转变”、“烦恼”等,只不过人们往往习用而不知罢了。佛教词汇数量之巨,在汉语专科词中是首屈一指的。有人统计,仅佛经中的“名数”一类,即有三千多个。佛教词汇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它兼有专科词、外来语和古语词三种形态,有特殊的宗教内涵和表现形式,并且同普通词汇交叉影响,成为人们阅读古代文献的难关。本文拟从佛教词汇的渊源、理论和组成等方面,作一些粗略的阐述和分析。
佛经的译传,肇始于汉末。经过五百余年至盛唐时期,编成《开元释教录》,藏经初具规模,凡五千余卷。佛经卷帙浩繁,义理艰深,输入了许多外来的新概念,在中国僧人著书立说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新词汇。魏晋士人多能说几句胡梵新语。《世说新语·政事》记载:“任大喜悦,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佛教新词汇的流行,对僧俗交往、佛法研究等,造成了理解上的一些不便。译经初兴,“文过则艳,质甚则野”(《大唐西域记》);且译师们在翻译和解释上,多有分歧。有些人好用中土玄学术语附会译解。如早期的佛学专著《牟子理惑论》以“无为”为“涅槃”。该书又以佛老并举(“睹佛教之说,览老子之要”),谓佛陀“蹈火不烧,履刃不伤”,显然是用《庄子》中的“姑射神人”曲为比拟。又如法琳《辩正论》云:“菩提者,汉言大道也”。《六度集经》译“真如”为“本无”。诸如此类,皆以玄释佛。中土译经,以后汉安世高为先。“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道安《大十二门经序》)。他的译经,属于朴直的“古译”,惜乎“时有不达”,如译“受”为“痛”,译“正命”为“直治”等。其后,又有支谦等绮丽的“旧译”。“旧译”派好用意译面多有失误。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杰出的译师为佛经译语的规范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那时,对译师的要求也提高了。在知识条件上,要求译师“言通华梵、学综有空”,“能诠不差、所显无谬”,“文诠三藏、义贯五乘”,“傍涉文史、工缀典词”;在品格条件上,要求译师“沉于道术,不好名利”,“器量虚融,不好专执”(见《翻译名义集》卷一)。在朝廷支持下,先后设置了若干规模较大的译场。如后秦姚兴迎鸠摩罗什于长安’开设草堂寺译场。罗什领导的义学僧有八百多名,重译经籍,辞义通明(见《魏书·释老志》)。罗什质而能文,多用音译纠正支谦意译之失,“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僧睿《大品经序》)唐代高僧玄奘精通汉梵,学识渊博,译笔严谨,所译佛典,既信且达,史称“新译”。《法苑珠林·传记》说他“翻译经论千有五百,尽善尽美,可称可赞”,并非虚誉。玄奘在译经实践中,总结出“五种不翻”,确定了音译或意译的标准(见《翻译名义集序》):
(1)多义词。如“薄伽梵”,具六义,故不翻。
(2)新名物词。如“阎浮”、“迦陵频伽”,中土所无,故不翻。
(3)沿用已久,约定俗成。如“阿耨菩提”,亦不翻。另外两种,是专从宗教角度所定的标准:
(4)“秘密不翻”。如诸经中的陀罗尼(密咒)。
(5)“尊重不翻”。如“般若”、“菩提”。当时,一部经的译成,要经过口译、笔受、校对、润色等程序。在正确的理解、有利的条件以及严格的要求下,译词日趋准确,翻经渐臻完善,揭开了我国翻译史上灿烂的篇章。
译经事业的发达,促进了佛教“小学”的产生和繁荣。一些兼通佛、儒的僧人,开始总结佛教词汇,系统研究其音义。隋唐以降,为佛经作音义的专著渐多。其中,以玄应、慧琳两家的《一切经音义》最负盛名。《玄应音义》久湮藏经中,罕为人知;《慧琳音义》久佚,直到晚近才被重新发现。两家《音义》被清代小学家奉为“显学”。庄炘推崇它们“实与陆(元朗)、李(善)抗行,良足贵矣。”(《唐一切经音义序》)两书体例,略似《经典释文》,而引证尤详;所引郑玄《尚书注》,贾逵、服虔《春秋传注》,李巡、孙炎《尔雅注》等数十种书,今均亡佚。两书除收佛教语外,还收了许多经籍中的普通语词,故深为一般语言学者所重视。宋代法云编的《翻译名义集》七卷,为佛学外来语的集大成者。该书专收借词,凡二千余条,注明异译,广泛引证,其解释较《一切经音义》更为详尽。此外,还有我国最早的双语词典、唐代义净的《梵唐千字文》;佛教基础类书、宋代道诚的《释氏要览》与明代的《三藏法数》;还有《华严经音义》、《法华经为为章》等专经音义。这些佛教“小学”著作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佛教本身。近现代,仍有不少佛学辞典陆续问世,如《佛教大辞典》、《佛学大辞典》、《实用佛学辞典》、《佛家名相通释》、《法相辞典》和《佛教人名辞典》等。
值得一提的是,梵语的传入,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形成和发展。《成唯识论》卷二:“说名句文,依声假立”。古印度“五明”中的“声明”,即相当于语言学;可见,梵语作为拼音文字,是特别重视声韵的。《通志略·六书略·论华梵》指出:“切韵之学,自汉以前人皆不识,实自西域流人中土。”如《说文》等,皆用直音。唐代智广《悉昙字记》谓:“其始曰悉昙而韵有六,长短两分,字十有二……声合韵而字生焉”。汉字的“反切法”便是受梵语拼音的启发,利用两个方块字,以“声合韵”,注出无穷之字的读音。《通志略·七音略序》云:“华僧从而定之以三十六为之母,重轻清浊,不失其伦”。唐末守温据以制定的以若干汉字为标记的汉语声母系统,奠定了等韵学的基础。此外,佛经的转读还促进了南朝声律学的发展。
佛教以“言亡虑绝”(《三论玄义》卷上)为至极,然而,也不否认语言文字的方便妙用,所谓“言说之极,以言去言”(《起信论》卷上)。在印度瑜珈佛学体系“五位百法”中,立有“文身、名身、句身”三种“不相应行法”(见《百法明门论》)。“三身”是对语言现象的归纳。“身”是汇集之义。“文身”指字母系统。(《成唯识论》卷二:“文即是字”);“名身”指词汇(同上:“名诠自性”);“句身”指句子系统,即文章等(同上:“句诠差别”)。字母的组合(文身)形成音声,音声表达种种概念(名身),通过概念的组合表达意见(句身),这就是“三身”的内在联系(见《大智度论》卷四八)。
名身是“施设众名,显示诸有”(《楞伽经》卷四)的。《大乘义章》卷一指出:“以名呼法(事物),法随名转,方有诸法种种差别,假名故有,是故诸法说为假名”。这就是说,词汇是标记种种事物概念的符号系统——假名。作为符号的名身,并不完全等于事物本身。如“火”是名,本身无热之用,故曰“假名”。佛家的“假名”说,揭示了名实的辩证关系,犹如《庄子·逍遥游》所说:“名者,实之宾也。”作为概念的名身,其对象是万事万物,前者是主观的,而后者是客观的;所谓“相为所诠,而名为能诠也”(《楞伽经》)。《成唯识论》卷八指出名身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表达抽象概念的“表义名言”和表达具体事物的“显境名义”。名身不但有“随物合成”的本义,而且有“随事转用”的引申义(见《大唐西域记》)。《瑜伽师地论》卷十五指出,一个规范的“假名”,应该具备“相应”、“义善”和“轻易”等要素。因明学认为,名身是感觉的抽象和综合,即从“现量”而来的“比量”。词语的作用是表达、交流,确切地说,属于“为他比量”。因明的三相说又指出了名身的内涵和外延的划分。词的内涵,必然包含它所应有的一切性质和功能,即“遍是宗法”。上位概念必然包括所有的下位概念,即“同品定有”。不同类的种属,必然互不相容,即“异品定无”。(见《因明人正理论》)
关于合成词的构造和词汇间的关系,佛家有“六离合释”。其中,有五种构词分析:
(1)持业释。从体用关系立名。如“藏识”,“识”是“藏”之体,“藏”是“识”之用。又如“发电机”,“机”是物体,而“发电”则是该“机”的功用。
(2)依主释。从主从、依正关系立名。如“眼根”,由“眼”得“根”,“眼”是主,“根”是从。又如“器界”,因“器”立“界”,“器”是正,“界”是依。
(3)有财释。从所具内涵立名。如“觉者”,“觉”为“者”之“财(内涵)”;“唯心论”,“唯心”为“论”之“财”。
(4)相违释。从联合关系立名。如“微妙”、“神通”,系由相对的同义词根构成;如“生灭”、“厌欣”,系由相反的反义词根构成。
(5)带数释。从标数概括立名。如“三学”(戒、定、慧),“五蕴”(色、受、想、行、识)。当然,有些词汇能兼数释。“六离合释”还有两种是表示词汇间的关系的:
(1)邻近释。表示同义关系。如“慧”——“念处”,“道”——“趣”,“泥洹”——“涅槃”。
(2)相违释(与构词法的相违释有区别)。表示反义关系。如“空”——“假”,“烦脑”——“菩提”,“平等”——“分别”。
关于词汇的表达形式,佛家有遮、表二诠之说,即否定式和肯定式。《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三谓:“遮谓遣其所非,表谓显其所是……如说盐,云‘不淡’是遮,云‘咸’,是表;说水,云‘不干’是遮,云‘湿’是表。”佛家以“破执”为宗,惯用否定式的辩证思惟。如“不二”、“不但空”、“不动解脱”,“非有”、“非非想”、“非色非心”,“无明”、“无生忍”、“无住涅槃”等。继承中观学派的三论宗干脆以“八不中道”为标榜,即“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因此,否定式的遮诠在表达佛教概念上至为重要。
在分析佛教词汇的组成之前,必须指出,随着佛经的传译,产生了许多新的普通词汇。这些语词不属于专科词范畴,有些直到今天还是常用词。我们不妨例举若干最早出现在经籍中并且沿用至今的语词:
希望 谴责 (《大品般若经》) 赞助 享受 评论(《佛本行集经》)
充足 消化 (《涅槃经》) 储蓄 厌恶 (《俱舍论》)
享福 惬意 援助 (《五分律》) 控告 傲慢 机会 (《大智度论》)
至于上文所举“世界”、“实际”、“烦恼”等。因有宗教内涵,仍应视作专科词。在敦煌变文中,也保存了不少俗语方言(见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作者(行家) 排打(赏玩) 恶发(发怒) 立地(立刻) 头头(事事物物)
佛教语与普通词汇之间,有着互相影响的转化关系。我们可以概括为承上转化、启下转化和承上启下转化三类。
(一)承上转化。即普通语词的佛教专科化,犹如“旧瓶装新酒”。例如:
法——《荀子·非相》:“圣王有百,吾孰法焉?”佛家借以意译Dharma,即教说、规范,亦泛指一切事理。
空——《后汉书·陈蕃传》:“田野空,朝庭空,仓库空。”佛家借以谓因缘和合,无我无常;义近“幻”、“假”。如《中论·观业品》:“虽空而不断,虽有而不常。”
声闻——本指名誉。《韩非子·内储说上》:“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佛家借以译指闻佛声教而悟入四谛的小乘圣者。
作业——《史记·高祖本纪》:“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佛家借以意译Karma,特指能引生果报的身口意活动。
(二)启下转化。即佛教专科词的语词化。例如:
实际——《智度论》卷三二:“实际者,以法性为自证。”今则泛谓客观现实、实践。
真空——《行宗记》卷一:“真空者,即灭谛涅槃。”今则以荡然无物为真空。
正宗——《云峰悦禅师语录序》:“不受燃灯记莂,自提三印正宗。”后则泛谓学业、技艺之嫡传者。
种子——法相宗指藏识中能引生现行法的功能。后特指植物的种子。今更有其他比喻义。
变相——原指表现佛经故事的图画。今则犹言“换汤不换药”;即改变形式而不改变内容。
(三)承上启下转化。即普通语词转化为佛教专科词,又转化为新的普通语词。该类词汇,体现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例如:
同居——古指家庭中尚未分家的兄弟等,犹言同藉、同财。《汉书·惠帝纪二》:“今居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天台宗借以指凡圣杂居的国土,为四佛土之一。今则特指男女两性结合的共同生活。
西方——古代泛指日落的方向。《诗·邶风简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净土宗专指弥陀净土。今多特指欧美诸国。
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佛教语与普通语词的关系。这种分类还是比较概略的。实际上,两者间的引申、转化关系还要复杂些。
从来源分,汉语中的佛教专科词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借词、译词和自造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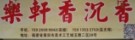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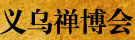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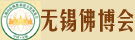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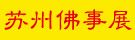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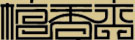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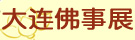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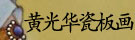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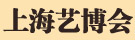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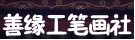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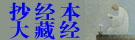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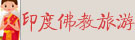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