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青峰绵延,间有一山名曰“瑞龙”,花香鸟语,竹茂林丰。风景绝佳处,隐出一寺来,寺由山名,唤作“瑞龙寺”,佛光祥瑞,香客往来不绝。佛家信缘,自北宋乾德四年(966)以来,这座千年古刹与多少人在风花吹过后擦肩而过,又与多少人在香火昌明处因缘缔结。传常便是其中一位。
清光绪十一年(1885),外国列强的枪炮强行轰开了禁闭的国门,软弱的清政府对于列强无休止的野心唯唯诺诺,局势一片动荡。才为世出,世亦需才。偏居南隅象山县城的一户汪姓人家,似乎身避桃源一般,全然不受纷飞战火的洗礼。家里添一男丁,满屋一片喜悦祥和。而这男婴,即后来的传常和尚。
尚年幼时,小传常便失去了生母。到七岁,他也和其他孩子一样,跨人了城里一家私塾读书。这个世道还算公平,虽然老天无情地夺走了疼爱他的母亲,却赋予了他聪慧的天资。在私塾里,传常每每会得到老师的盛赞和同学们的羡慕。好景不长,丧偶的父亲不久便续弦,以为能给传常延续无微不至的母爱。俗话说:后娘的拳头,云里的日头。在私塾先生和同学眼中聪明优秀、样样都能的小传常在继母看来,却是眼中钉、肉中刺,万般不得相容。在私塾里春风得意的他每次回到家都要遭到继母无端的痛斥甚至毒打。饶是他聪明万分,也难以得到继母一丝的怜爱。
有压迫就有反抗。终于他在十二岁时,不堪继母百般虐待,愤然离家出走。一时的意气用事,在外处处碰壁。于石浦行贩,不想消折了本钱,生活难以为继,原先的血气方刚被现实打击得一败涂地。传常无奈返家,几日不得饭食,行经东溪时,终因体力不支,饿晕在路边。天不绝人,当时恰好有一老妇人打那路过,见此情形,心生爱怜,便把随身携带的饭粥予以他吃。传常谢别老妇人后便至南庄小东洋,觅得一户欧姓富贵人家,讨得份放牛的差事。因其勤勉,不久为雇工,便在欧姓人家里住下。
许是天意造化,十八岁时,传常来到河东瑞龙寺,得敏兆和尚收留,遂奉敏兆为师,得赐法名传常,便在寺中参研佛法,广行善举,终日与晨钟暮鼓为伴。心安乐处即身安乐处。一晃已过五六载,敏兆和尚见弟子精明干练,天资可人,便把县城城隍庙、西寺以及瑞龙寺悉数归传常持理。传常也不负恩师厚德,自甚俭约,常日粗衣劣食,而不妄自费用一钱。且更兼有一手精于化募的本事,也因其行善之德,百姓广为响应。积十余载,寺庙财用充足,便使钱修缮三寺庙,加高屋栋楼宇,兴建西寺东西两廊,重建东首地楼,整顿北隅静院。又新建佛殿香堂,增塑金刚佛像,外植修竹乔松,把整个寺庙弄得别致出新。民国六年(1917),传常再次募捐修葺瑞龙寺。是时,寺庙共占田地约千亩,房屋二百余间,且兼有布庄、染坊等设施。
传常忆及昔日东溪老妇人饭粥之德,往而寻之不可得。无处可报恩,传常便开辟院址,购进住宅,并亲自奔赴温州运回上等杉木建材,又得钱文梅等人相赠的毛巾、衣物等资助,创办起孤儿院,把此恩德泽被苍生。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该院正式更名为佛教孤儿院,已收容孤儿达百人,另外还开设一所小学,其间有教师三人,凡培养孤儿至十六七岁时便让其出院,其中较聪慧者,还资助他们上中学,乃至大学。
民国三十年(1941),县城沦陷,且疫病横行,因霍乱而死者不可胜数。传常看在眼中,便与同乡人萧伯元一起,在汤家祠堂开设时疫医院,并聘请十名医务人员为患者诊断医治。及时的妙手施恩,使患者颇多获救。民国三十六年(1947)夏天,久未得寸雨,田地大旱不得耕种,水源枯涸不得灌溉,百姓苦不堪言。上苍有好生之德。传常于是在县城东门外及秧田头选了两处,独自出资开挖了两口水井,遂解百姓缺水之难。翌年3月,传常因其广修善行,被选为县佛教会理事长。传常致力于公益事业,受其恩惠者,自仕途宦海之人乃至卑田院乞儿,皆同等相待。周遭百姓素闻其高义,都慕名而来。传常一一热忱接应,常年极少有闲暇之时。新中国成立后,传常遣散孤儿院众,各归故里。他历任县人大代表,闲居静休颐养天年。1966年,传常患病离世,享年八十二岁。
传常一生,以纯朴示人,轻蔑奸邪小人,心胸开阔,明辨是非,所以人都愿和他往来、谈论事宜,而恶俗之流敬畏其威严,亦不敢相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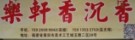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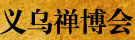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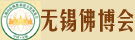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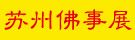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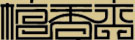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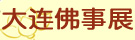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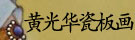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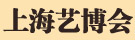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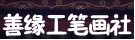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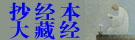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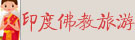

 )
)



